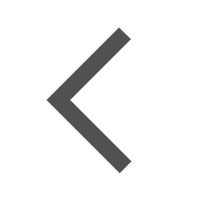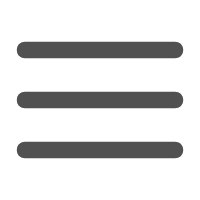东北粘豆包。
“别拿豆包不当干粮”是家乡人认为不该轻视什么时,常说的一句话,可见豆包在东北人尤其是黑龙江人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。在家乡,豆包大致有两种:一种是用小麦面粉(白面)做皮子的,一种是用粘米面做皮子的。
我特别要说的就是粘米面做皮子的粘豆包。
粘豆包起源于山西,后来山西移民闯关东时传入东北,成为当地人喜欢的食品,并延续了下来。
我小时候,偏远农村很缺少白面,而粘豆包虽不易消化却抗饿,所以,在农活儿累的时候,大多农家都以粘豆包为主要劳动力的食物,吃闲饭的还没资格每餐享受呢。
我不知道别人家的粘豆包是怎样做出来的,但我却无数次亲见并参与了我家粘豆包的制作过程。
其实,粘豆包的原材料主要就两样东西,即粘米面(黄米面)和饭豆(芸豆),后来,才有糯米和粘苞米加工出来的豆包皮子。每次做粘豆包都是先将粘米面用水和好,放在盆里发酵,等发好了,再将烀熟碓碎的饭豆团成牛眼珠大小的豆泥丸儿,放进已捏成手心大小的粘米面皮子里包起来,团成近椭圆形状,再把接触屉布的一端弄得稍平,均匀地摆放在铺了湿润屉布的笼屉上,等水烧开了,放进锅里蒸。十五到二十分钟,就可以起锅。烀好的豆馅儿里常放糖精提升口感。
包粘豆包这活儿,看似简单,其实想包得好看又不漏馅儿也不易,别看粘米面熟了粘糯得很,生时却极松散不易聚拢,一不小心就包坏了包丑了。做什么都要样儿的母亲常叮嘱我们精心着点儿,别包得三扁四不圆、稀淌花漏的。
每次,母亲将香气腾腾的大锅揭开盖子,端出腾云驾雾的笼屉,那整整齐齐的金黄的豆包就呈现在眼前,非常匀称,一水水儿地露着浑圆而闪着亮光的圆乎乎的头,身子却早紧密地连在了一起。
起锅之后,要趁热将它们分离开,否则,凉了硬了,就分不开了,硬分就会开膛破肚子。那粘乎乎的一片,即便热时分,如果不采取恰当措施也是分不利落的。母亲总是舀一碗凉水,将筷子蘸上凉水,再插到两个豆包之间去夹开,夹的时候,得看准,万一夹偏,就会有破肚子的。如此循环往复,直至将整笼屉的粘豆包一个个地起完。这样分出来的粘豆包,表面完整光滑。粘豆包蒸的时候是立着的,蒸熟夹开后再放到盖帘子上则需倒立,这样做是因为,在起的过程中,光滑的圆顶已经被空气吸收干了表面的水分,将这一面着地放下去,已不容易粘连了。
起先,看着母亲有板有眼地做这些的时候,就开始佩服劳动妇女的聪明了,而当我自己也能亲手做,则满心自豪。
那时候,和别人家一样,我家一到冬天经常蒸粘豆包,一般晚上却很少吃,母亲说,粘豆包硬,不好消化,再说,吃完那么禁饿的东西就睡觉压炕头子白瞎了。
吃粘豆包蘸白糖更好吃,如果家里没有白糖,就必须得就咸菜,否则,会烧心(其实是烧胃)。
说来也奇怪,在热着的时候无比粘的粘豆包,一旦凉了,就几乎彻底地失去了粘力。手里拿个凉的粘豆包,一掰就下来带白茬子的硬块儿,这可真是一切状态的维持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客观条件啊,失去那个条件,该状态也就成为无本之木。
小时候,有时在外面疯饿了,回家找吃的没有,我就会跟弟弟妹妹潜入仓房,抓出来几个母亲准备不时热着给我们吃的冻粘豆包,一点儿一点儿地啃吃,别看冰凉梆硬的,啃起来却既有趣儿又解饿,特别是在啃到豆包馅儿的时候,就像要解放哪个孤岛一样地兴奋而有成就感。
粘豆包的确好吃,可也不是谁都能吃得的,比如,镶了假牙的,那牙口儿要是不牢固,一口粘豆包就能把牙给拽下来。如果年岁大的,吃了不好消化就会胀肚子,所以,想亲口尝尝粘豆包,一定要先了解注意事项才行。
即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在,粘豆包靠着自身的魅力,不但经久不衰,还百变其身,不断翻新花样儿,豆包皮子由只有大黄米面逐渐发展到糯米面、粘苞米面等;原来纯豆馅儿或加糖精,后来糖取代了糖精;原来只有蒸吃的吃法,如今则在传统吃法上至少增添了将蒸好的粘豆包再用油煎了的吃法。
粘豆包,过去是因为紧缺而被珍视,如今则是因为求精而被追捧,从一个粘豆包的前世今生,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再提高。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