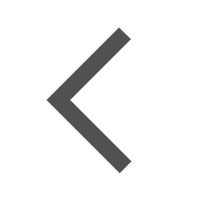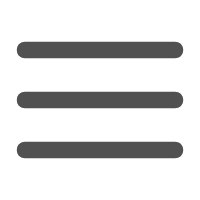□陈晓林
癸卯年以来,先后购买了刘梦溪的《陈寅恪的学说》(第二版)和《八十梦忆》,王富仁的《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——〈呐喊〉〈彷徨〉综论》和《中国现代作家印象记》,陈平原的《书里书外》(增订版)、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(增订版)和《刊前刊后》。暇日捧读,深感兴趣。
三位先生都是研究文史和现代文学的大家,在专业方面,我是一脚门里,一脚门外,只能赏读,不好置喙。但书中若隐若显的思想光芒,却时常让我在阅读中或拍案击节,或陷入沉思。
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这一出自《增广贤文》的名言,为旧时读书人奉为圭臬。有感于时下读书人面临的“大环境和小环境”,陈平原先生把这句名言修改为:两耳闻窗外事,一心读圣贤书。
只去掉两字,兼顾了书斋与窗外,一下子天地宽阔,血脉贯通。在陈先生看来,好多北大老前辈之所以一路走来步步莲花,恰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关紧门窗,而是兼听“风声”“雨声”与“读书声”。
陈平原先生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,读他的书,容易使人想起“觉醒年代”中那些老北大的先生们。
陈平原主张读书要“坚守自家的阅读立场”,要警惕自己的人生被“模式化”。陈平原认为,为了建立自家的阅读立场,防止被“模式化”,必须学会“拒绝”与“遗忘”。其中批判的功能格外重要。借用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话,读书人须不断追问:“从来如此,便对么?”陈平原先生主张追问和反省,不仅包括具体结论,而且敢于追问和反省大人物。
“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”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,传为启功先生所拟并书,早已闻名遐迩,可曾为北师大教授的王富仁先生却不以为然。他认为“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”格局小了,一个“范”字把什么都罩住了,限制住了,如果让他来起草校训,就直接把“师”、“范”两字去掉,就叫:学为人,行为世。
启功和王富仁两位先生都已作古,恕我不恭,从旁观者角度看,启功先生拟写的校训己足够精辟,然而我更喜欢王富仁先生的“修改版”。王富仁先生是新中国有学位制度后第一位文学博士。只可惜,王富仁先生走得早了些。他生前留下这样一段话:“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。关键在于,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,活得更有意义一些,活得更像一个人。”
与王富仁和陈平原二位先生相比,刘梦溪则是著作等身的老先生了。但刘先生的思想却始终保持着鲜活度,近些年屡屡给读者以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之惊喜。
刘梦溪先生在《八十梦忆》一书中,《我的一次学术历险》一文中讲述了一段往事,大约在1994年或者1995年,刘梦溪在杭州参加一学术会议。当时先生因写《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》一文,正对学术独立着迷,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,学者不一定去耗时费力管学术以外的事情。读到此,我陷入沉思,有话想说,但还是不说也罢。
丁聪先生为文化人造像,像后例有自述及友朋附语。刘梦溪先生的自述是:“吃麦当劳,喜欢柳如是,研究中国文化。”季羡林先生赠语是:“博古通今,颖慧而且谨严。相互切磋,莫忘那更好的一半。”
读书读的是知识,悟的却是思想。语言只是思想的外壳,语言的深度由思想深度决定,语言的宽度由思想的宽度决定。我喜欢读思想容量大,有思想锋芒的书。上述三位先生的书,均属于此类。